案头那方端砚已伴我十载。晨起研墨时,指腹抚过砚堂的冰纹,总觉那些青灰色的脉络里藏着呼吸。墨锭与石面相触的沙沙声漫开,像春蚕啃食桑叶,又似细雨打湿青瓦,恍惚间能看见墨汁顺着纹理游走,在砚池里晕成一片朦胧的云。
这方砚台原是外祖父的珍藏。他书房西窗下的紫檀木架上,它曾与古籍、铜炉为邻,砚盖内侧刻着的 “守静” 二字,笔锋里藏着柳体的筋骨。幼时我总爱趁他午睡,偷偷掀开砚盖看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,以为是某种神秘的符咒。直到某个梅雨季的午后,外祖父握着我的手教我研墨,才知那些纹路原是匠人用刻刀与时光共同写下的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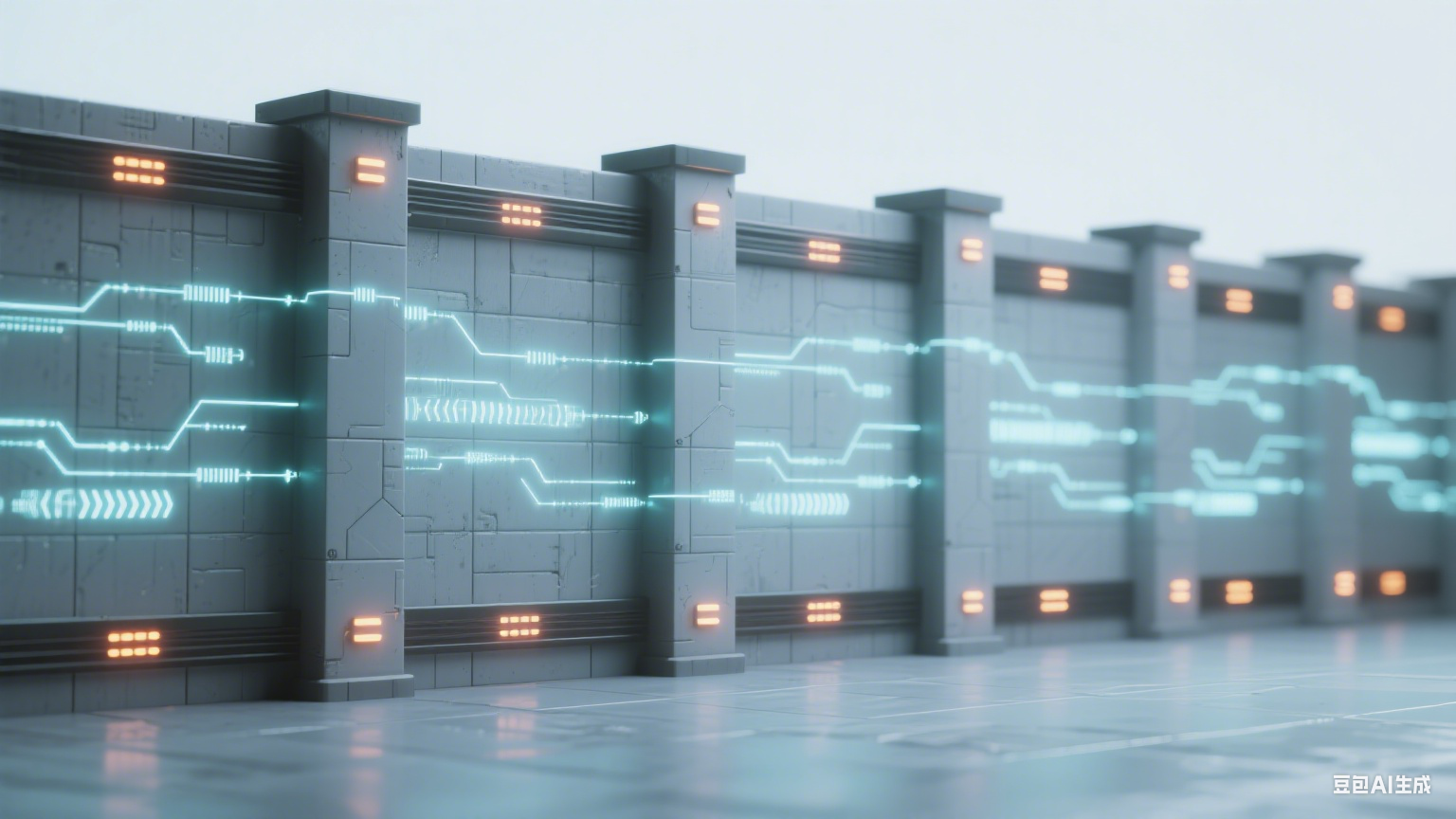
外祖父说,好砚需得 “石质坚润,发墨如油”。他年轻时在肇庆寻访砚坑,曾见老坑石在月光下泛着青紫色的莹光,石肉里的冰纹像极了冻结的溪流。匠人采石时要匍匐在狭窄的坑洞里,一锤一凿都得顺着石纹的脉络,稍有不慎便会损了整块石料的灵气。这方砚台的砚堂保留着天然的弧度,边缘却雕着细密的缠枝纹,据说是民国年间一位无名匠人耗时三月才完工。
我真正学会品砚,是在二十岁那年的深秋。外祖父卧病在床,让我取来砚台研墨。他说,砚台最忌干涸,需得时常滋养,就像人要常怀温润之心。我握着墨锭缓缓研磨,看墨汁在砚池中渐渐浓稠,忽然懂得那些冰裂纹路里藏着的岁月。外祖父用颤抖的手写下 “砚寿千年”,墨迹未干便溘然长逝,留下满室墨香与这方沉默的砚台。
此后每逢雨天,我总爱取出砚台细细擦拭。砚盖内侧的 “守静” 二字已被摩挲得发亮,砚池边缘的缠枝纹里还留着经年累月的墨痕。有时研墨至深夜,看灯光在砚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,竟会生出错觉,仿佛外祖父仍坐在对面,看我笨拙地握着笔,说墨要磨得匀,字才立得住。
去年冬天整理旧物,在砚台的夹层里发现一张泛黄的纸条。是外祖父的字迹,写着 “石有灵性,需以心养之”。墨迹早已干透,却像一滴墨落在心湖,漾开圈圈涟漪。原来那些年他总在研墨时出神,不是在看墨,是在与这方砚台对话。
如今案头的砚台仍在。春夜研墨时,窗外的雨声与砚上的沙沙声交织,墨香里仿佛能闻见外祖父书房里的旧时光。偶尔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未落,看砚池里的墨汁映出自己的影子,忽然明白,所谓传承,原是让器物带着人的温度,在时光里慢慢生长出灵魂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