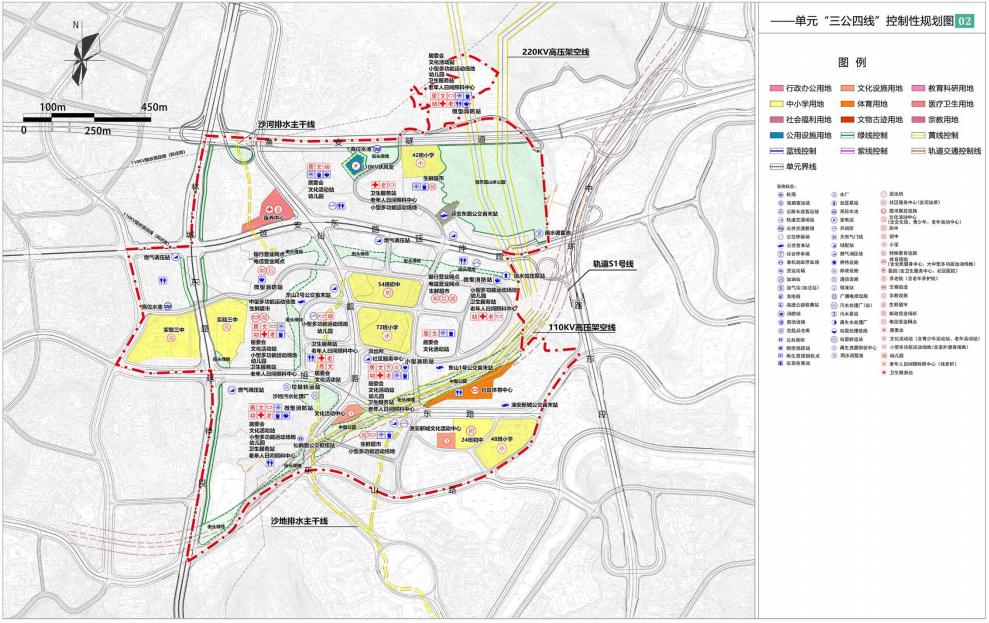
老城区拆迁公告贴出来那天,我蹲在青石板路上数砖缝里的青苔。墙根处那株长了二十年的爬山虎正把卷须探进窗棂,玻璃上还留着去年冬天呵出的雾汽,母亲用指腹画的小兔子尾巴被雨水洇成淡青色,像块融化的薄荷糖。
推土机轰鸣着碾过巷口时,我摸到砖墙上凹进去的小坑。那是十岁那年摔破膝盖,血珠滴在青砖上晕开的印记,后来每次经过都要伸手按一按,仿佛能摸到当年结痂时的痒。如今砖块松动得厉害,指尖陷进去半寸,带出些潮湿的土腥味,像谁在低声叹息。
转角的骑楼总在梅雨季渗出细密的水珠。二楼木窗的插销早锈成红棕色,却仍能听见风穿过回廊时的呜咽。去年深秋有位穿蓝布衫的阿婆在这里晒腊肠,竹匾里的油星子滴在地面,晕出深浅不一的琥珀色。现在竹匾躺在废墟里,腊肠的油香混着尘土味,成了最后一道告别的宴席。
博物馆新馆的玻璃幕墙映着流云。阳光穿过钢结构的骨架,在地面拼出镂空的光斑,像谁把老房子的窗棂拓在了地上。展柜里陈列着拆迁时抢救出的木梳,梳齿间还缠着半根灰白的发丝,标签上写着 “民国二十年制”,却没说清它曾在多少个清晨,穿过哪位女子的发间。
胡同深处的四合院总在黄昏时亮起灯笼。门墩上的小石狮子被摸得溜光,嘴角的弧度藏着几代人的体温。去年冬天,我看见有位老人对着结冰的水缸出神,哈出的白气在朱红的门框上凝成霜花,像幅被岁月冻住的画。
长江边的老码头还立着锈迹斑斑的吊臂。木质的跳板被江水泡得发胀,踩上去会发出咯吱的呻吟,像在诉说那些被浪涛卷走的日子。有次涨潮,我看见块碎瓷片卡在木板缝里,青花的纹路浸在水里,随波晃动成片模糊的蓝,像谁哭花了的眉眼。
古镇的石板路被磨得发亮。雨后的水洼里能看见飞檐的倒影,翘角上的瑞兽望着天,嘴里像含着没说出口的往事。巷尾的茶馆还在用铜壶煮茶,水汽漫过窗纸,把里面的笑谈晕成片朦胧的暖,让人想起小时候趴在奶奶膝头听故事的午后。
教堂的尖顶总在钟声里微微震颤。彩绘玻璃把阳光滤成斑斓的雨,落在长椅的木纹上,像谁打翻了调色盘。第三排左数第二个座位,椅面有块深色的印记,是多年前某位新娘的婚纱拖尾留下的,如今仍能想象出那天裙摆扫过地面时,扬起的细碎光斑。
村口的老槐树围着圈青石板。树根在石缝里盘虬卧龙,把岁月长成看得见的模样。树下的石碾子早不转了,碾盘的凹槽里积着落叶,风过时簌簌作响,像在数那些坐在碾子上纳鞋底的黄昏。有片树皮剥落的地方,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,是五十年前两个孩子的约定,如今仍守着树,守着没说尽的话。
旧校舍的窗台还摆着缺角的瓷瓶。爬山虎的叶子在玻璃上投下晃动的影,像谁在黑板上没擦净的板书。后排靠窗的位置,桌角刻着道浅浅的刻痕,是当年用圆规尖划下的,如今指尖抚过,还能想起那个盯着窗外流云发呆的少年,和他没做完的数学题。
寺庙的红墙爬满了薜荔。墙根的苔藓总带着湿漉漉的绿,像谁没擦干的眼泪。香炉里的灰烬积了厚厚一层,风过时卷起细尘,在阳光里跳舞,恍惚能看见无数双手合十的影子。石阶被踩得凹陷,每个凹处都盛着虔诚的温度,让人想起那些跪在蒲团上的晨昏,和心里说给菩萨听的悄悄话。
老宅的天井总在雨天泛着水光。青石板拼成的地面像块巨大的砚台,承接天上的云,也承接檐角的泪。堂屋里的太师椅还摆着原来的模样,椅垫上的牡丹被磨得褪色,却仍能看出当年针脚里藏着的温柔。墙角的鱼缸早就没了鱼,只剩些绿藻在水里摇晃,像谁遗忘在时光里的梦。
那些被推倒的墙,被拆走的梁,被运走的砖,其实都没真正离开。它们变成了城市上空的尘埃,变成了风中飘散的气息,变成了某个瞬间突然涌上心头的钝痛。或许有天你走过新盖的大楼,会在某个转角闻到熟悉的木香味,那是老房子的灵魂,在和你说声,别来无恙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