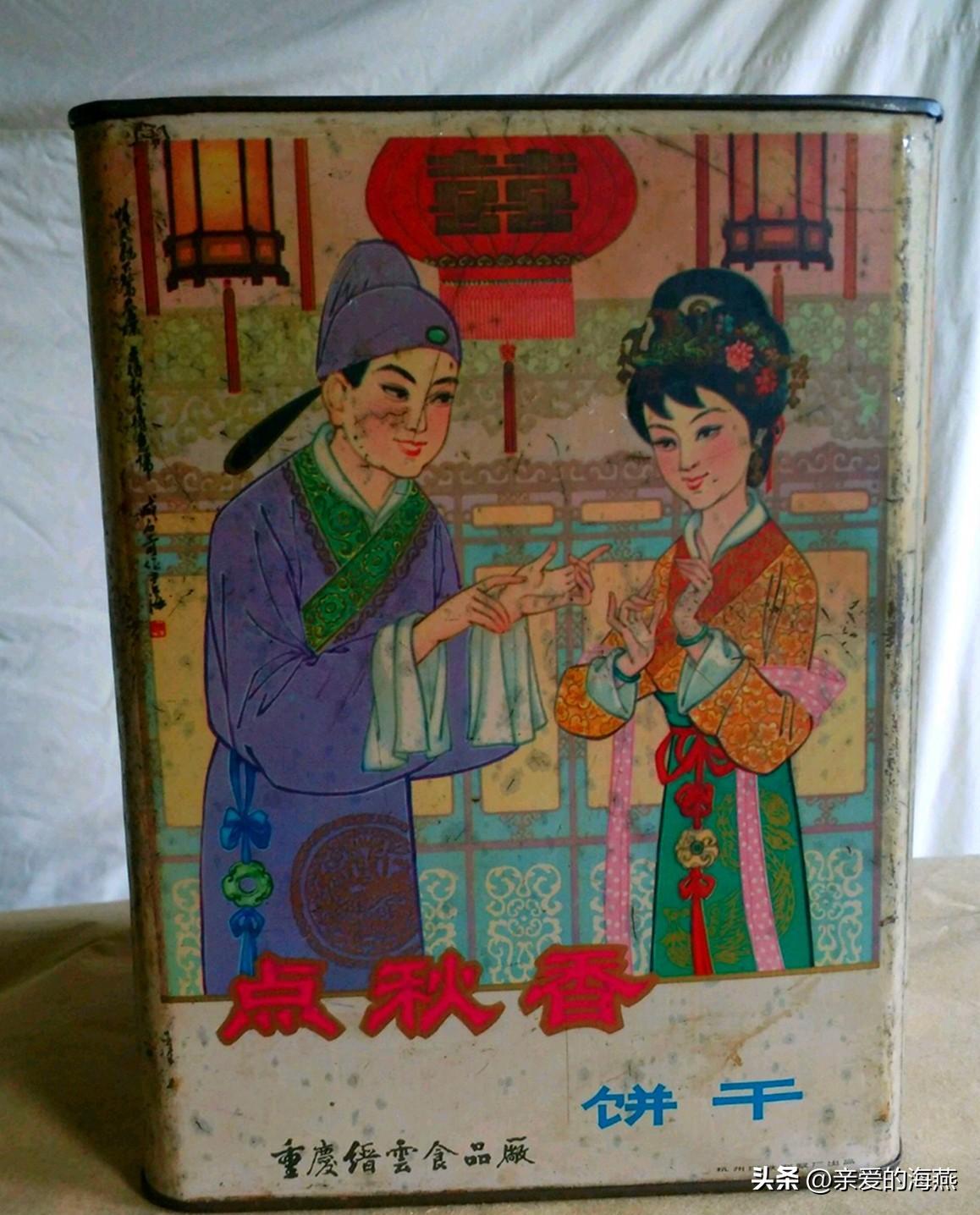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时,总能在巷尾瞥见那顶褪色的蓝布帐篷。帐篷下的木架用麻绳捆着松脱的边角,几排书脊在潮湿的空气里泛出深浅不一的黄,像晒了半世纪的烟叶。守摊的老张总坐在小马扎上,膝盖上摊着本线装的《聊斋》,眼镜滑到鼻尖也懒得推。
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摊,是因一本缺了封底的《小王子》。硬壳封面磨出毛边,内页却留有工整的批注,某页空白处画着朵歪歪扭扭的玫瑰,旁边写着 “1987.5.23 赠明”。老张说这书搁了快十年,原主是个总穿白衬衫的姑娘,每周末都来换书,后来突然再没出现过。他用袖口擦了擦书脊上的灰,“有些书比人长情,守着守着就成了念想”。

往后每个周末,我总绕路去摊前晃悠。老张的书从不按类别摆,武侠小说旁可能挤着本医学词典,泛黄的诗集底下压着褪色的连环画。有次在《百年孤独》里翻出张电影票根,1998 年的《泰坦尼克号》,座位号是 13 排 7 座。老张说这书是个老头卖给他的,老头总念叨当年带老伴看这场电影时,她偷偷抹眼泪把爆米花撒了一身。
书摊的书大多来路不明。有时是搬家的人嫌麻烦清出来的,有时是废品站里捡漏的,偶尔也有特意送来的。上个月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,抱着本《哈利波特》站了半天,最后红着眼圈放在摊上说:“妈妈说看闲书影响学习。” 老张没问缘由,只是在她走后,把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,旁边放了块小木板,写着 “免费借阅,记得还”。
雨天的书摊最有味道。雨水敲打着蓝布帐篷,发出沙沙的声响,混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,倒比咖啡馆的香薰更让人安心。有次下暴雨,我和老张一起把书往塑料布底下挪,他突然指着本《边城》说:“这书里夹着张船票,1983 年从凤凰到长沙的。” 纸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凤凰花瓣,颜色褪得几乎看不见,却像能让人想起某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午后。
常来的老主顾里,有个戴助听器的退休教师,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出现,背着手一本本翻看历史书。他说年轻时在乡村教书,带着学生们在煤油灯下读《史记》,现在眼睛花了,却还是想摸摸那些有温度的纸页。还有个开面包店的老板娘,每天收摊后过来,站着读几页散文,她说揉面包时想起书里的句子,发酵的面团都好像更香甜些。
老张不爱说话,却记得每个顾客的喜好。知道我喜欢散文,每次收到新的散文集,总会留出来摆在角落;知道退休教师研究民国史,遇着相关的旧书,会特意用牛皮纸包好。有次我翻到本 1956 年版的《野草》,扉页上有行钢笔字: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。” 字迹力透纸背,像是带着书写者当年的热忱。老张说这书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,摊主说原主是个老教授,去世前还在病床上翻这本书。
书摊的木板上,总有些奇怪的标记。有的书脊上画着小太阳,老张说是适合晴天读的;有的画着月亮,是留着晚上看的;还有本《红楼梦》,旁边画着个哭脸,他说这书太悲,看的时候最好备着纸巾。有次我问他这些标记有什么用,他嘿嘿笑说:“看书和交朋友一样,得讲缘分,标记清楚了,好让它们找到对的人。”
上个月城市改造,巷尾要拓宽马路,书摊被划进了拆迁范围。老张没抱怨,只是每天收摊后,多花半小时把书整理得更整齐些。最后一天摆摊时,老主顾们都来了,退休教师送了他一幅自己写的字,写着 “书香满巷”;面包店老板娘带来刚出炉的肉桂卷,说:“就当提前庆祝乔迁之喜。” 那个送《哈利波特》的小姑娘也来了,手里抱着本《绿山墙的安妮》,说:“这次是妈妈让我来的,她说看好书不影响学习。”
搬家那天,我们帮老张把书搬到临时租的车库里。他蹲在地上整理那些书,突然指着本《飞鸟集》说:“你看,这里夹着张照片。” 黑白照片上,两个扎麻花辫的姑娘并肩坐在柳树下,手里都捧着书,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背面写着 1972 年夏,旁边还有行小字:“我们要读遍天下书,走遍天下路。” 老张把照片小心地夹回书里,轻声说:“说不定哪天,照片上的人会找来呢。”
现在的书摊搬到了更远些的巷子里,蓝布帐篷换成了更结实的帆布,木架也重新刷了漆,却还是老样子。旧书们挤在一起,带着各自的故事,等着被翻开。老张依旧坐在小马扎上,膝盖上换了本《浮生六记》,眼镜还是滑在鼻尖。路过的人偶尔会停下脚步,从那些泛黄的纸页间,撞见某个陌生人的青春、遗憾或是未完成的心愿。
有本《汪曾祺文集》里,夹着张便签,上面用铅笔写着:“栀子花粗粗大大,又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‘去你妈的,我就是要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?’” 字迹歪歪扭扭,却透着股可爱的倔强。每次翻到这页,总能想起老张守着书摊的样子,不管世界怎么变,他和他的旧书们,都在那里自顾自地散发着光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