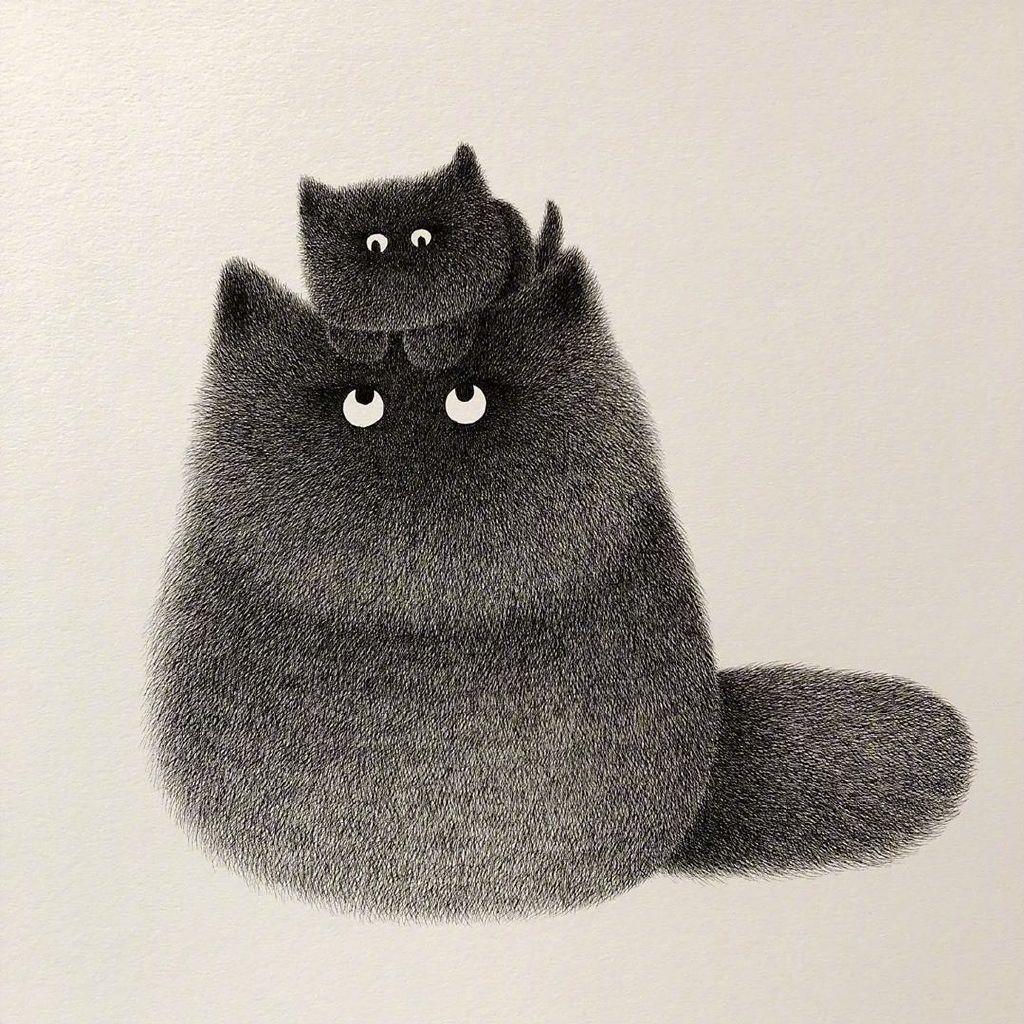祖父的老座钟总在午后三点发出格外清晰的声响。阳光斜斜切过雕花木框,在钟摆下方投下细长的影子,像根被拉长的银线,一头拴着 1987 年的蝉鸣,另一头系着我掌心的温度。
那年我刚够着座钟底座,踮脚时能看见玻璃罩里的黄铜钟摆左右摇晃。祖父总说这钟摆是有灵性的,晴天摆得轻快,阴雨天就沉缓些,比气象台的预报还准。他修理钟表的铺子开在巷尾,木头招牌上 “修记” 两个字被雨水浸得发乌,却在每个清晨准时卸下门板。我常蹲在铺子角落看他工作,镊子捏着细小的齿轮在台灯下闪光,座钟的滴答声混着他哼的评剧调子,成了童年最安稳的背景音。

祖父的手指总带着机油味,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渍。他给座钟上弦时格外郑重,钥匙插进钟侧的孔里,顺时针转三圈,再逆时针回半圈,动作像在进行某种仪式。“这钟跟了我三十年,” 他边擦钟面边说,“比你爸岁数都大。” 玻璃罩上的花纹早已被擦拭得模糊,却能映出我和祖父重叠的影子,一个白发稀疏,一个羊角辫翘得老高。
1992 年的梅雨季来得特别凶,巷子里的积水漫过脚踝。那天祖父修的是台德国挂钟,齿轮卡得厉害,他趴在工作台上捣鼓到后半夜。我被雷声惊醒时,看见他正用绒布擦老座钟的玻璃罩,钟摆的影子在墙上晃成个椭圆。“明儿水退了,带你去买糖画。” 他说话时,我发现他左手小指缠着纱布,渗出血印子。后来才知道,他为了捡掉进座钟底座的小弹簧,被碎玻璃划了道口子。
座钟第一次出故障是在我十岁生日那天。本该敲响的午时十二点,它却哑了嗓子。祖父急得满头汗,把钟整个拆开,零件摆了满满一桌子。他戴着老花镜,鼻尖几乎碰到齿轮,我蹲在旁边数他掉在桌上的白发,一共七根。修到傍晚,当第一声钟鸣透过纱窗飘出去时,巷口卖冰棍的张婶探进头来笑:“修师傅,你家钟比广播还准时。” 那天的生日面是祖父用搪瓷碗装的,卧在面上的荷包蛋颤巍巍的,像座钟摆锤上的红绸子。
我去省城读高中那年,祖父把座钟调到了北京时间。临走前他教我认钟摆的节奏:“慢三下是晨雾,快五下是晚风。” 宿舍床头的电子钟总在夜里发出细微的嗡鸣,我常常在那声音里想起老座钟的滴答,像是祖父用手指轻敲桌面的节奏。第一个寒假回家,推开门就听见十二声钟鸣,祖父站在钟旁搓着手笑,他鬓角的白比钟摆的铜锈还显眼。
祖父中风那天,老座钟停在下午三点十七分。我赶回家时,看见他躺在藤椅上,手指还保持着拧发条的姿势。座钟的玻璃罩裂了道缝,是他摔倒时碰的。街坊帮忙把他抬上救护车,经过铺子门口时,我听见钟摆晃了两下,发出 “咔嗒” 轻响,像声叹息。在医院陪护的那些天,我总在凌晨三点十七分醒来,窗外的路灯透过玻璃照进来,在墙上投下细长的影子,和记忆里座钟下的光影重叠。
祖父没能再回到他的铺子。出院后他瘫在轮椅上,说话含糊不清,却总指着墙角的座钟咿咿呀呀。我试着给钟上弦,它却像赌气似的不肯走。直到某天清晨,我发现祖父用还能动弹的右手,正费力地擦拭钟座上的灰尘,阳光照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上,像撒了把碎金。那天下午,我抱着座钟去找巷尾新来的修表师傅,小伙子摆弄了半天摇头:“零件太老了,配不到。” 回来看见祖父正对着停摆的钟流泪,浑浊的泪珠砸在玻璃罩上,晕开一小片水雾。
去年秋天整理旧物,我在座钟底座摸到个硬物。拆开底板才发现,里面藏着个铁皮盒,装着我小时候掉的乳牙,祖父修表用的小镊子,还有张泛黄的纸条,是他用铅笔写的:“丫头十岁生日,钟摆快了两秒。” 铁皮盒底层压着张黑白照片,二十多岁的祖父站在刚挂起的 “修记” 招牌下,怀里抱着崭新的座钟,笑得露出虎牙。照片边角卷了毛边,像被反复摩挲过。
现在老座钟摆在我的客厅里,玻璃罩的裂缝用透明胶带粘着。我没再找人修它,就让它停在那个下午三点十七分。有时阳光好,我会把祖父的藤椅搬到钟旁,自己坐在对面,想象他还在擦拭钟面。风穿过纱窗时,偶尔能听见零件松动的轻响,像是钟摆还在摇晃。上个月请人来打扫,保洁阿姨想把钟挪个地方,我伸手按住底座,忽然发现木纹里嵌着些细小的齿轮碎屑,像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秘密。
前两天整理祖父的病历,在最后一页发现张便签,是护士代笔的,写着祖父清醒时说的话:“钟摆红绸子要系活结。” 我搬来梯子查看座钟内部,果然在摆锤上发现半截红绸,结打得松松的,轻轻一碰就散开了。夕阳透过玻璃裂缝照进来,在红绸上投下道金光,恍惚间,我仿佛听见十二声钟鸣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穿过蝉鸣、雨声、卖冰棍的吆喝,落在此刻的客厅里,溅起细小的回声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