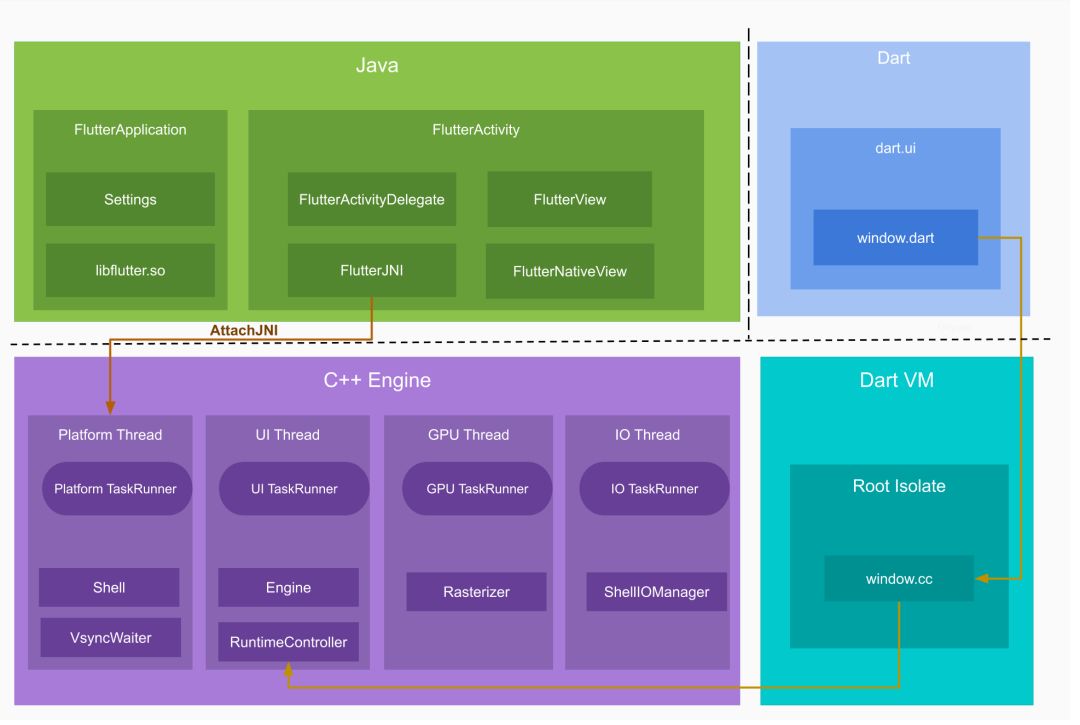月光漫过窗台时,总会在地板上洇出一块潮湿的光斑。我常常赤足踩在那片微凉里,听胸腔里传来的钝响,像老式座钟漏了油的齿轮,每一次转动都拖着半秒迟疑。某个人的笑声会突然从齿缝间钻出来,带着春日樱花被碾碎的甜腥,然后又被更深的寂静吞没。
抽屉深处压着半张褪色的电影票根,边角蜷曲如风干的蝶翼。十七岁那个暴雨夜,我们挤在影院最后一排,看女主角在雨里摔碎眼镜。你突然凑过来咬我耳朵,说镜片裂开的纹路像极了老家屋檐的冰棱。散场时你把伞塞给我,自己冲进雨幕,
白衬贴在背上,勾勒出蝴蝶骨振翅欲飞的形状。如今那把伞的金属骨架早已锈成红褐色,却还在每个梅雨季,从伞面褶皱里渗出淡淡的樟脑香。
镜子里的人总在午夜变换模样。有时眼角会多出一道细纹,像被谁用指甲轻轻划开的裂痕;有时瞳孔深处会浮起一片海,浪涛声裹着某句没说出口的再见。我数过镜中人的睫毛,左边七十四根,右边七十二根,比去年秋天少了六根。它们掉落在洗脸池里,混着牙膏泡沫打转,像一群溺水的白蝴蝶。
旧毛衣的袖口磨出了毛边,凑近闻能嗅到晒过太阳的干草味。去年冬天你穿着它来敲我的门,围巾上沾着雪粒子,进门就往我手心里呵气。我们坐在地毯上拆礼物,你送的手套食指处有个破洞,说是故意留着方便我玩手机。后来那只手套在地铁上弄丢了,剩下的那只总在寒潮来时,在衣柜最深处发出细碎的响动,像谁在轻轻叩门。
巷口的梧桐树又落了一层叶,扫街的老人总在黎明前把它们堆成小山。有次我蹲在树影里数落叶的脉络,发现每片叶子的纹路都藏着一句密语。第三十七片叶子上写着 “等”,第一百零九片写着 “忘”,而压在最底下的那片,叶柄处还留着半个牙印 —— 那是你去年咬过的,说要给树做个标记。风过时整堆叶子都在发抖,我突然听懂它们在说什么,却被呛得蹲在地上咳了很久。
冰箱里还冻着去年的荔枝,果皮皱得像老太太的手背。你曾说最喜欢看荔枝在水里解冻的样子,果皮裂开时会发出细碎的声响,像谁在轻声说爱你。某个失眠的凌晨,我把它们全倒在水槽里,看绛红色的壳慢慢舒展,露出半透明的果肉。水珠顺着指尖往下淌,在瓷砖上积成小小的水洼,映出天花板吊灯摇晃的影子,像沉在水底的月亮。
衣柜顶层的纸箱里藏着半罐薄荷糖,铁盒上的漆掉了大半。你走那天把它塞进我包里,说晕车时含一颗会舒服些。后来每次路过高铁站,我都会摸出一颗捏在手心,看糖纸在阳光下折射出虹彩。薄荷味在舌尖炸开时,总能想起你某次感冒,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,却坚持要给我讲冷笑话,说这样能让笑声驱散病毒。
阳台的仙人掌开了朵白花,花瓣薄得像宣纸。去年你说它活不过三个月,赌输了要请我吃火锅。如今花茎歪歪扭扭地顶着那朵花,像举着个易碎的梦。我每天给它浇半杯水,看根须从盆底的孔里钻出来,在瓷砖上织成细密的网。某个清晨发现花瓣落了一片,夹在日记本里,成了今年夏天最轻的标本。
手机相册里存着三百二十一张天空的照片,从靛蓝到鱼肚白,每种颜色都标记着日期。你曾说喜欢看云的形状,说每朵云都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。有次暴雨过后,西边的云被染成橘红色,你举着手机跑了三条街,说要追上那片像鲸鱼的云。现在每次抬头,总会下意识摸口袋,才想起手机换了新的,那些照片早就随着旧手机,躺在废品站的某个角落。
地铁站的广告牌换了新的画面,某个角度看过去,女主角的侧脸像极了你。有次我在站台等车,看广告牌的灯光在人群脸上明明灭灭,突然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片海。有人的海在涨潮,有人的海结了冰,而我的那片海,总在某个瞬间掀起巨浪,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,都卷成深海里的沉船。
抽屉里的磁带还在转,只是录音机早就坏了。你送我的那盘卡带,A 面录着我们在山顶喊的回声,B 面是某个午后的雨声。有次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,磁带像瀑布般卷出来,在阳光里闪着银光。我蹲在地上慢慢把它们绕回去,手指被割出细小的伤口,血珠滴在磁带上,晕成小小的红梅。
街角的咖啡店换了老板,新煮的拿铁总带着焦苦味。以前我们总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梧桐叶落在玻璃上。你喜欢往咖啡里加三颗糖,说这样苦中带甜才像生活。现在每次路过,都能看见那个位置坐着不同的人,他们对着手机笑,或者盯着窗外发呆,没人知道那里曾有过两杯咖啡,在暮色里慢慢凉透。
换季时整理旧物,翻出你织了一半的围巾,毛线在竹针上绕成乱糟糟的团。你说要织成星空的颜色,却总在收针时出错。某个雪夜你坐在沙发上拆线,毛线球滚到我脚边,像只白色的小猫。现在那团毛线还在衣柜里,偶尔会滚出来,在地板上留下弯弯曲曲的痕迹,像谁在写一封没有结尾的信。
雨又下了起来,敲打着玻璃窗发出沙沙的响。晾在阳台的衬衫被风吹得摇晃,衣角扫过栏杆,像谁在轻轻挥手。我数着窗上的雨痕,看它们慢慢汇成小溪,在玻璃上画出交错的河。突然想起你说过,每滴雨都是天空的眼泪,落进海里就成了盐。那么此刻,有多少颗眼泪正在敲我的窗,又有多少片海,正在谁的眼眶里涨潮。衫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