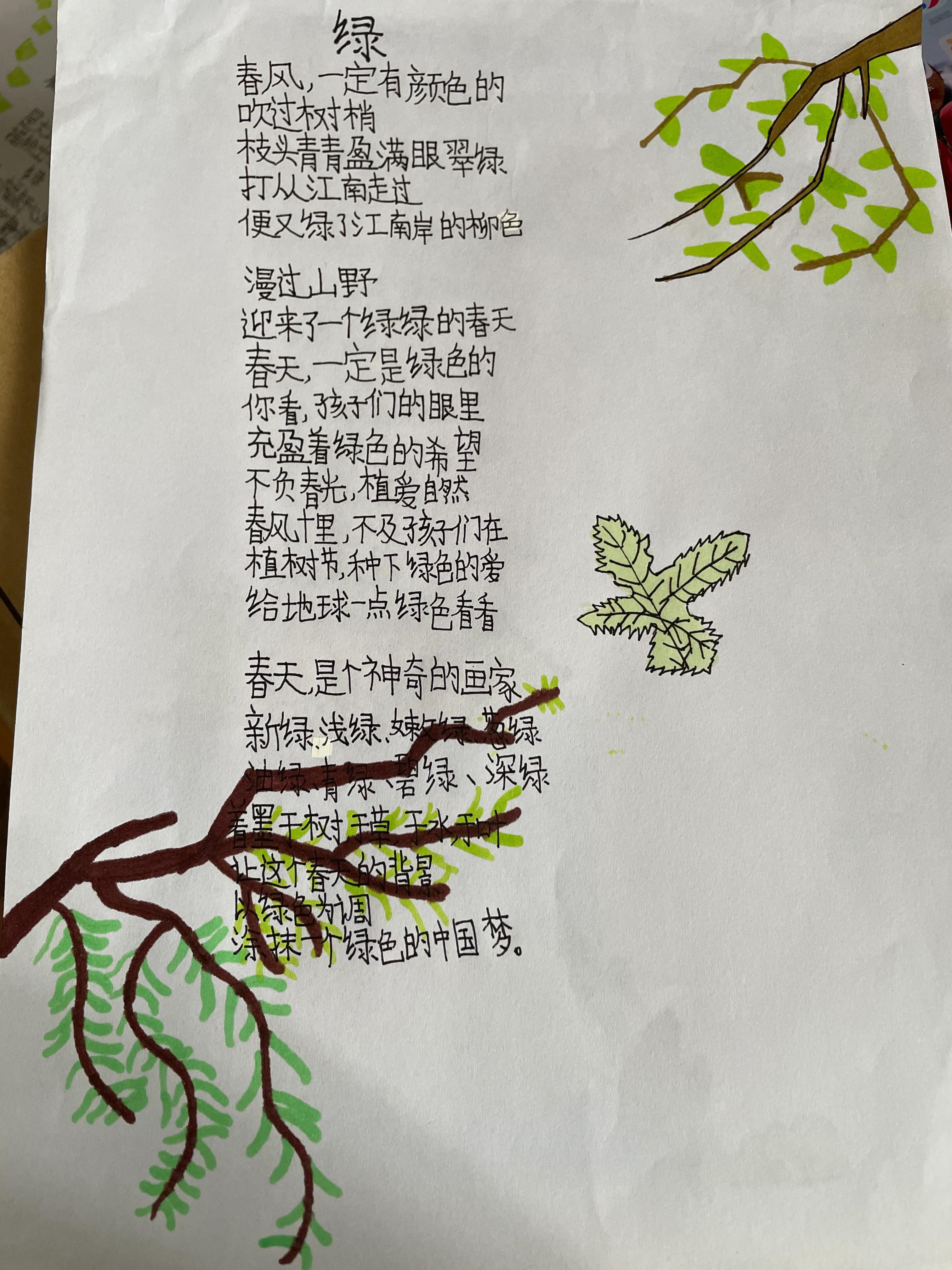
阁楼天窗漏下的光斑,在积灰的书脊上缓缓移动。第三排最左端那本牛皮封面的诗集,书脊已磨出细密的裂纹,像某种爬行动物蜕下的皮。我伸手抽出它时,指腹触到扉页里夹着的干枯银杏叶,脆得仿佛一碰就会化作金粉。
这是祖父留下的书。他的钢笔字迹在空白处洇开淡蓝的云,“霜降读此页”“檐雨敲窗时重读”,那些批注比诗句本身更像散落的星子。某页右下角有团模糊的水渍,边缘泛着浅褐,或许是他当年临窗喝茶时不慎打翻的龙井,茶香早散了,却把时光泡成了琥珀。

梅雨季节来临时,书脊会微微膨胀。我总在这时想起祖父书房的樟木箱,他说旧书需要呼吸,就像老屋的木梁要在潮湿里舒展年轮。有次暴雨冲垮了后墙,一箱线装书浸在泥水里,他蹲在雨里一页页揭晾,指尖泡得发白,倒像刚从水墨里捞出来。
书里夹着的票根正在褪色。1957 年的电影院存根,边缘齿状如断锯,上面的钢笔字写着 “与婉华同看”。婉华是我从未谋面的祖母,名字总在祖父醉酒后伴着叹息浮出水面。那些被虫蛀的书页间,似乎还藏着他们隔着书脊的低语。
蝉鸣最盛的午后,我常在书页间发现意外的收藏。半片干枯的桃花瓣,想必是某年春分夹进去的;褪色的火车票根,终点是早已消失的小站;甚至有粒被虫蛀空的莲子,轻轻一摇,能听见时光在里面打转的声响。这些细碎的物件,像散落在墨色里的星子,照亮了被文字遮蔽的岁月。
祖父的批注总在不经意处动人。读到 “柴门闻犬吠” 时,他在旁边画了个歪扭的小狗,尾巴翘得老高;某首悼亡诗的空白处,只有两个浅淡的字:“懂得”;而在那些描写月光的段落旁,总有用铅笔淡淡涂抹的痕迹,仿佛想把月光留在纸页上。这些不成体系的笔迹,比任何传记都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人的模样。
有次台风过境,老屋的西窗被吹破,雨水漫进书房。我抢救那箱旧书时,发现最底层压着本没有封面的日记。某页记载着 1963 年的雪夜,祖父用煤炉烤橘子,橘香混着墨味漫了满屋;另一页画着株腊梅,旁边标注着 “婉华手植,今岁始花”。墨迹在岁月里晕染,像朵永不凋谢的花。
书脊上的烫金渐渐剥落,露出底下暗红的布面,像老人手背暴起的青筋。我学着祖父的样子,在梅雨季节把书搬到廊下晾晒。阳光穿过书页间的缝隙,在青砖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那些文字仿佛活了过来,在光影里轻轻摇晃。风过时,整排书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在低声交谈。
去年深秋整理旧物,在《东坡志林》的封底发现个信封。里面装着片干枯的枫叶,叶脉清晰如网,衬着泛黄的信笺。祖父的字迹已有些颤抖:“今日见枫,忽忆昔年与汝母同游岳麓,彼时霜叶正红。” 没有署名,却让我想起他晚年常坐在廊下,对着虚空喃喃自语的模样。
冬夜围炉时,我总爱翻这些旧书。火光在书页上跳跃,把祖父的批注映得忽明忽暗。某页空白处,他用红笔圈出个小小的 “暖” 字,笔尖划过的力度,仿佛想把这个字刻进纸里。窗外落雪的声响,混着书页翻动的声音,让人恍惚觉得,那些逝去的时光并未走远,只是躲进了这些泛黄的纸页里,在墨香与尘埃的缝隙中,静静呼吸。
檐角的冰棱在晨光里融化,水珠顺着瓦当滴落,在青石板上敲出单调的节奏。我把晾干的旧书重新码回书架,最上层空出个位置,放进去今年新夹的玉兰花瓣。或许百年后的某个午后,也会有个人,在翻动这些书页时,忽然撞见今天的阳光,听见此刻屋檐下的雨声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