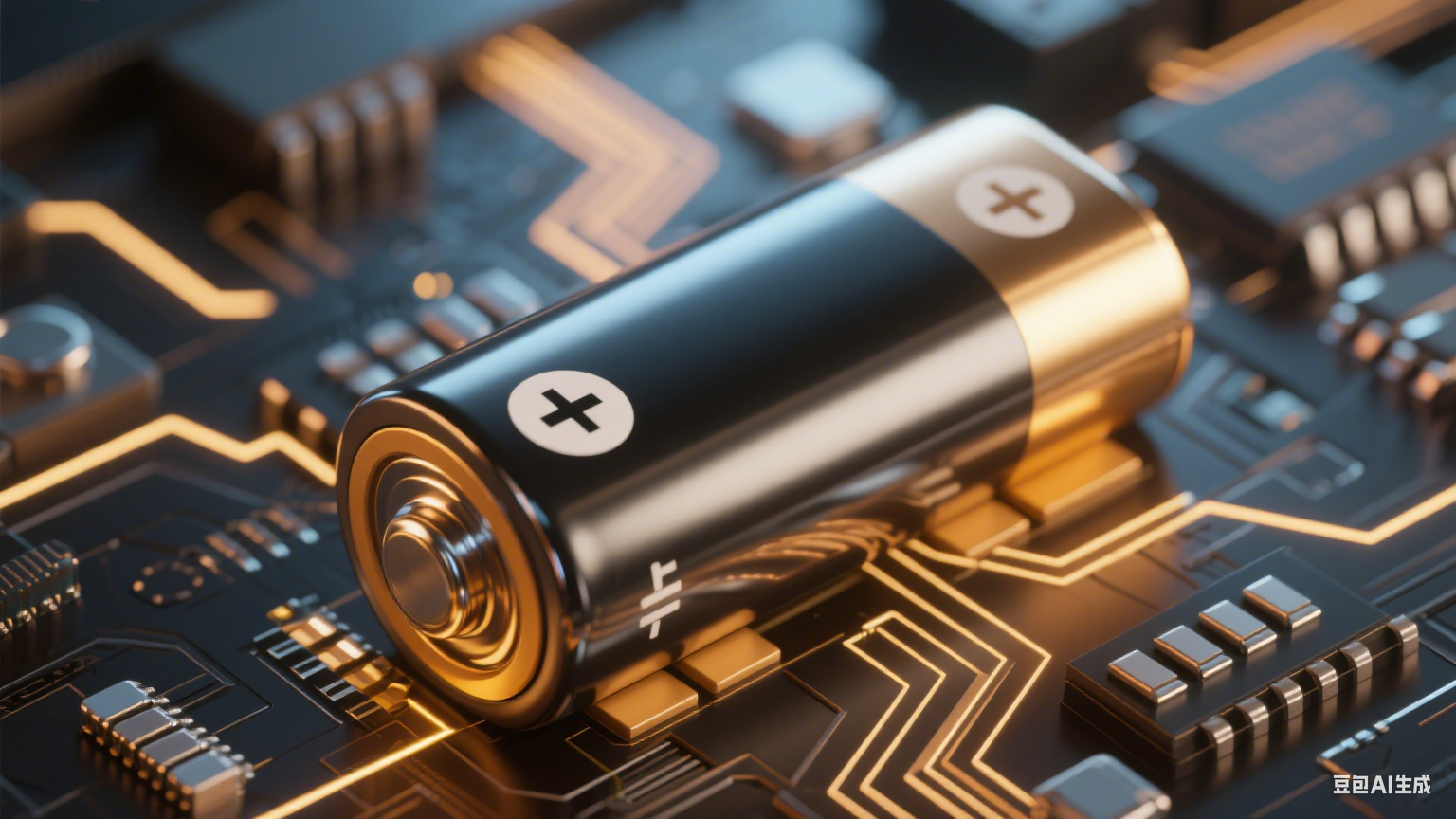梧桐叶把最后一缕阳光剪成碎金,空气里浮动着白日残留的温热。我坐在藤椅上数玻璃上的水汽,指腹划过的地方晕开一片朦胧,像极了老照片里褪了色的黄昏。远处的烟囱还在吐着白烟,被风揉成轻薄的纱,缠绕着渐暗的天际线缓缓上升。
街角的花店开始收摊,老板娘将褪色的玫瑰插进铁皮桶,花瓣上的水珠折射着路灯初亮的光。穿校服的女孩踮脚把最后一支康乃馨塞进竹篮,辫梢的蝴蝶结随着脚步轻轻摇晃,在石板路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暮色正沿着墙根悄悄蔓延,给晾在绳上的白衬衫镶上毛茸茸的金边。

河面上的碎光渐渐沉下去,像被谁打翻了装星星的匣子。钓者收起鱼竿时带起一串水花,银亮的鱼在网兜里蹦跳,溅起的水珠落进暮色里,瞬间就融成了墨。对岸的芦苇丛沙沙作响,惊起几只白鹭,翅膀划破靛青色的天幕,留下转瞬即逝的弧线,仿佛有人用毛笔在宣纸上扫过淡墨。
老钟表在客厅里咔嗒作响,摆锤摇晃的幅度越来越慢。奶奶把晒好的陈皮收进陶罐,指尖沾着橙黄的粉末,在玻璃罐壁画出浅浅的痕。八仙桌上的粗瓷碗还留着粥香,苍蝇停在蓝印花布上,翅膀被夕阳最后的余晖染成琥珀色,一动也不动,像被钉在时光里的标本。
晾衣绳上的床单在风里鼓起,像只褪色的大鸟要展翅飞走。我伸手去拽衣角,指尖触到布料上残留的阳光温度,忽然想起童年某个相似的黄昏,母亲也是这样牵着我的手,看晚霞漫过对面的屋顶。那时的天空总像块融化的蜜糖,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味道,如今再抬头,只剩深蓝渐次晕染开来,把所有往事都浸成了模糊的剪影。
巷口的修鞋摊开始收拾工具,铁皮盒里的钉子在暮色中闪着微光。老师傅把顶针套在布满老茧的手指上,动作迟缓却安稳,像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。旁边的梧桐树下,几个孩子还在追逐打闹,笑声撞在斑驳的墙壁上,又弹回来落进渐浓的夜色里,惊得栖息的麻雀扑棱棱飞起,搅乱了一整片温柔的深蓝。
厨房飘来饭菜的香气,混着晚风中的栀子花香,在鼻尖萦绕不去。我起身往回走,脚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,与远处传来的自行车铃铛声交织在一起,谱成一曲独特的黄昏小调。路过杂货店时,老板娘正把最后一瓶酱油摆上货架,暖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挤出来,在地上投下狭长的光斑,像谁不小心遗落的丝带。
天边最后一抹霞光也渐渐隐去,只留下几颗早亮的星星,在深蓝的天鹅绒上眨着眼睛。我站在院子里,看月光慢慢爬上晾衣绳,给那件未收的白衬衫镀上一层银辉。风穿过葡萄藤架,叶子沙沙作响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秘密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,又很快被夜色吞没,只剩下无边的宁静,温柔地包裹着整个世界。
或许每个黄昏都是时光的渡口,让白日的喧嚣在此靠岸,又让夜晚的静谧从此启航。我们站在这样的过渡里,既看得见昨日的残影,又能触摸到未来的轮廓。当最后一盏灯在巷尾亮起时,整个世界仿佛都屏住了呼吸,等待着什么,又像是在回味着什么,一切都在不言中,却又分明千言万语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