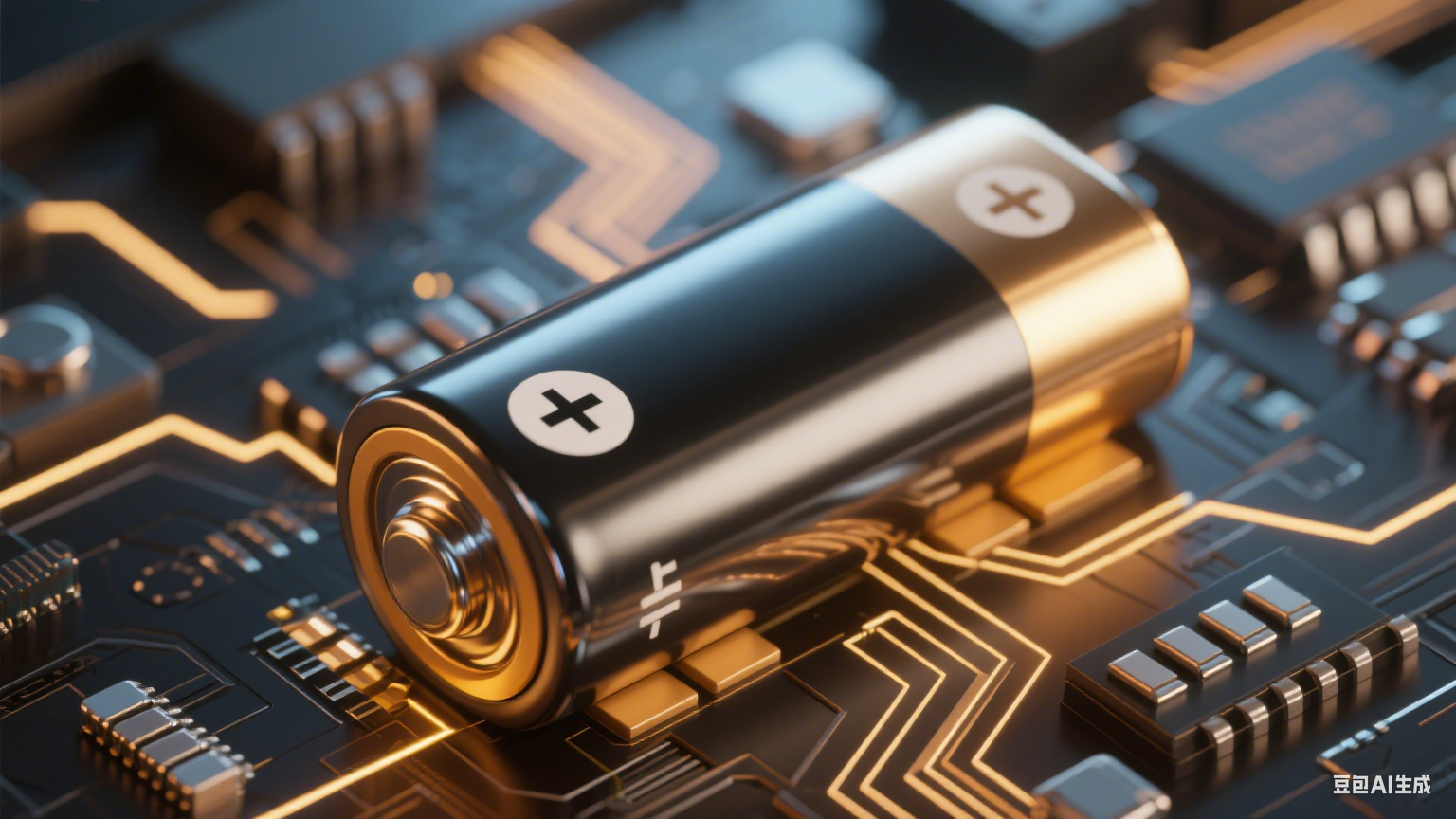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时,总能看见陈叔蹲在店门口用软布擦拭铜制门牌。“知阅堂” 三个字刻得很深,边缘的包浆在潮湿的空气里泛着温润的光,像块浸在时光里的琥珀。这是条藏在老城区褶皱里的巷子,两侧的骑楼墙皮斑驳,唯有这家书店的木质橱窗总擦得一尘不染,玻璃上贴着泛黄的牛皮纸,写着 “旧书换咖啡” 的字样。
我第一次推开那扇挂着铜铃的木门时,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惊飞了檐下的鸽子。店内弥漫着松节油和旧纸张混合的气息,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斜斜切进来,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,无数细小的尘埃正在光柱里跳舞。靠墙的书架高到顶棚,褐色的木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指痕,最高处摆着几本封面磨损的线装书,书脊上的金字在阴影里若隐若现。

陈叔那时正坐在柜台后的藤椅上,手里捧着本 1987 年版的《小王子》。听见动静他抬起头,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道月牙,指节叩了叩柜面:“随便看,找不着的书喊我。” 他的声音带着烟草和岁月沉淀的沙哑,像老式唱片机转动时的杂音,却让人莫名安心。
角落里的旧沙发陷着个温柔的弧度,扶手上搭着件深蓝色毛线衫。我后来才知道,那是陈婶的遗物。二十年前陈婶突发脑溢血,送医时紧紧攥着本《边城》,书里夹着他们年轻时在凤凰古城拍的黑白照片。陈叔说,现在每到阴雨天,总觉得书架后面有翻书的窸窣声,像她还坐在那里等他算账。
书店的老主顾里,有位姓周的退休教师。每天下午三点,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靠窗的位置,点杯不加糖的苦咖啡,从帆布包里掏出放大镜,一页页研读线装版的《史记》。周老师的老伴五年前得了阿尔茨海默症,认不出任何人,却唯独记得年轻时周老师给她读《史记》里 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 的场景。如今他每天读完书,都会把当天看到的故事记在笔记本上,晚上念给病床上的老伴听。
去年深秋,巷口开了家网红书店,落地窗前摆着 ins 风的绿植,扫码就能听有声书。有阵子知阅堂的客人少了很多,陈叔却照旧每天清晨五点起床,踩着露水去废品站淘旧书。他说有回在废纸堆里翻到本 1953 年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扉页上用蓝墨水写着 “赠给最勇敢的人”,字迹被泪水晕开了一小块,他当即用半个月的菜钱把那本书赎了回来。
冬至那天飘起了雪,我去知阅堂避寒,正撞见周老师在教几个孩子包书皮。孩子们捧着从网红书店买来的畅销书,叽叽喳喳地问怎么才能让书保存得更久。周老师慢悠悠地说:“书啊,就像人一样,得经常摸摸,聊聊,才能活得长久。” 陈叔在一旁烧着煤炉,火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明明灭灭,铜壶里的水开了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开春后,巷子里的樱花开了满树。有天傍晚,我看见陈叔站在樱花树下打电话,声音难得地带着雀跃。挂了电话他告诉我,周老师的老伴突然能认出人了,昨天指着书架上的《边城》,含糊地说想再听一遍。“我这就去把那本书找出来,包层新的书皮。” 他转身进店时,夕阳正穿过樱花的缝隙落在他肩上,像落了满身的星光。
现在每次路过知阅堂,仍能听见铜铃清脆的响声。有时是放学的孩子来换书看,有时是附近的老人来蹭杯热茶。网红书店的热度渐渐退了,玻璃门上的招聘启事换了又换,而知阅堂的木门依旧在每个清晨准时打开,陈叔蹲在门口擦门牌的身影,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前两天暴雨,我又去店里躲雨。陈叔正在给一本 1972 年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做修复,糨糊的气味混着雨水的潮气漫在空气里。他指着书里用铅笔写的批注给我看,字迹娟秀,在 “何当共剪西窗烛” 旁边画着小小的烛火。“这肯定是当年哪个姑娘写给心上人的。” 他笑着说,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着光,像藏着整个春天的星辰。
雨停的时候,夕阳把云层染成了橘红色。几个孩子举着刚换的漫画书从店里跑出来,踩得水洼噼啪作响。陈叔站在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,忽然轻声说:“你看,书里的故事跑出来了,就活在这些孩子的脚步声里呢。” 风穿过巷口,铜铃又响了起来,檐下的鸽子振翅飞去,掠过满墙的爬山虎,留下几片摇晃的影子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