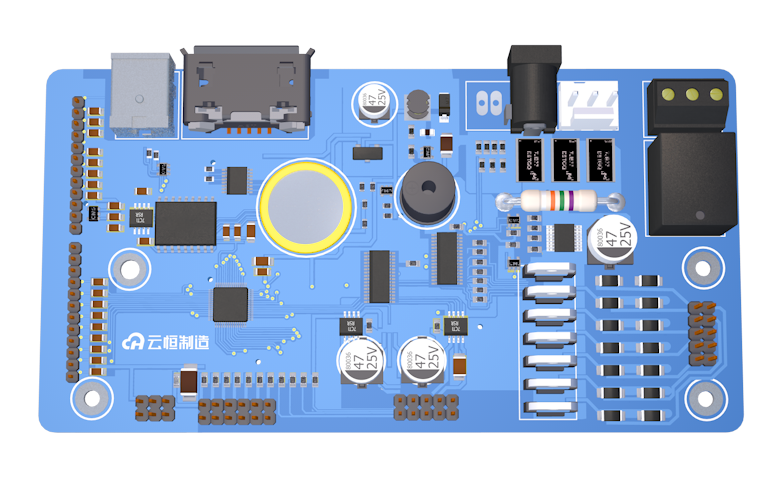那枚褪色的铜铃铛总在有风的夜晚轻响,像极了二十年前每个黄昏,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巷口时,挂在她自行车把上的声响。那时我总爱数她发间的碎光,以为那是太阳落在她鬓角的金粉,直到后来自己也长出第一根白发,才惊觉那些闪烁的,原是岁月悄悄系上的丝线。
记忆里的夏天总浸在井水的凉润里。母亲会把西瓜吊在井中浸半晌,傍晚提上来时,水珠顺着青绿色的纹路往下淌,在水泥地上洇出小小的圆。我踮着脚够案板上的水果刀,她总说 “慢点”,手掌却早已覆在我的手背上,带着洗过衣服的皂角香。刀刃切开瓜瓤的瞬间,甜丝丝的汁水溅在胳膊上,我们望着彼此沾着红瓤的指尖笑,蝉鸣在老槐树上铺成厚厚的毯。
后来我背着帆布包离开故乡,行李箱里塞满她连夜炒的南瓜子。站台上的风掀起她的衣角,她把皱巴巴的零钱塞进我口袋,说 “穷家富路”,眼角的纹路里盛着未说出口的惦念。火车开动时,我看见她跟着铁轨小跑,灰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舞,像株在风中摇晃的芦苇。那画面在车窗上晃成模糊的光斑,多年后仍会在某个加班的深夜,突然撞进脑海里。
孩子出生那天,母亲坐最早的长途汽车赶来。她抱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家伙,手指轻轻拂过那层胎毛,忽然红了眼眶。“当年你也是这么小,整夜整夜地哭,我抱着你在屋里来回走,天快亮时才敢合眼。” 她说话时声音发颤,我望着她鬓角新增的白发,突然想起那些被我忽略的清晨 —— 厨房飘来的粥香,晾在绳上带着阳光味的校服,还有她目送我上学时,站在门口久久未动的身影。
去年深秋带母亲去拍全家福,摄影师让她靠近些,她却总往后缩。“我这老婆子不上相,别挡着你们年轻人。” 她搓着衣角笑,眼角的皱纹挤成温柔的褶皱。我攥住她的手,才发现那双手早已不像从前那样光滑 —— 指腹结着厚茧,手背布满褐色的老年斑,手腕处还留着年轻时被开水烫过的疤痕。可就是这双手,曾为我缝补撕裂的书包带,曾在我发烧时一遍遍敷上凉毛巾,曾把最香的那块排骨悄悄夹进我碗里。
上个月带孩子回老家,小家伙缠着奶奶讲我小时候的事。母亲搬来藤椅坐在院里,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她身上,她的声音像浸了蜜:“你妈妈三岁时偷喝墨水,把舌头染得乌黑,哭着说自己要变成黑妖怪;上小学时把奖状贴满整面墙,睡觉前都要对着看半天;第一次领工资回来,买了件红毛衣给我,我舍不得穿,过年时才拿出来……” 她讲着讲着忽然停住,望着远处的田埂出神,“一晃啊,你都这么大了。”
孩子跑去找小伙伴玩,我坐在母亲身边,看她慢慢剥着橘子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两条紧紧依偎的藤蔓。“妈,明年我们去南方过冬吧,那边暖和。” 我轻声说,她却摇摇头:“不去啦,院里的月季还要人浇,你张奶奶每天都来喊我打牌呢。” 我知道,她是怕给我们添麻烦,就像从前无数次,她总说 “我没事”,却在挂了电话后,默默记下我随口提过想吃的家乡菜。
夜里哄孩子睡下,听见母亲在厨房窸窸窣窣。推开门看见她正往玻璃罐里装花生糖,那是我从小爱吃的零食。“超市卖的太甜,我加了点芝麻,你带回去给孩子尝尝。” 她抬头时,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泛着银光。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,就像小时候她抱我那样。她的肩膀比记忆中瘦小许多,隔着薄薄的棉布衫,能感受到脊椎突出的形状。那一刻突然想起龙应台的话: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不过是目送彼此的背影渐行渐远。可我分明觉得,那些被岁月拉长的距离里,始终牵着一根看不见的线,一头系着我日渐成熟的脚步,一头拴着她从未改变的牵挂。
窗外的月光淌进屋里,落在母亲新添的白发上。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同样的月夜,她也是这样坐在灯下,为我缝补磨破的鞋底。针脚在布面上开出细密的花,就像她藏在时光里的爱,从未说过惊天动地的话,却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,织成了最温暖的铠甲。
此刻孩子的呼吸均匀绵长,母亲的玻璃罐里传来花生糖的脆响。我悄悄起身掖好她们的被角,月光在地板上投下三道交叠的影子。或许真正的亲情,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,而是这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碎片 —— 是她鬓角的白发,是我掌中的温度,是孩子睡梦中喊出的 “奶奶”,是我们在漫长时光里,彼此照亮的模样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