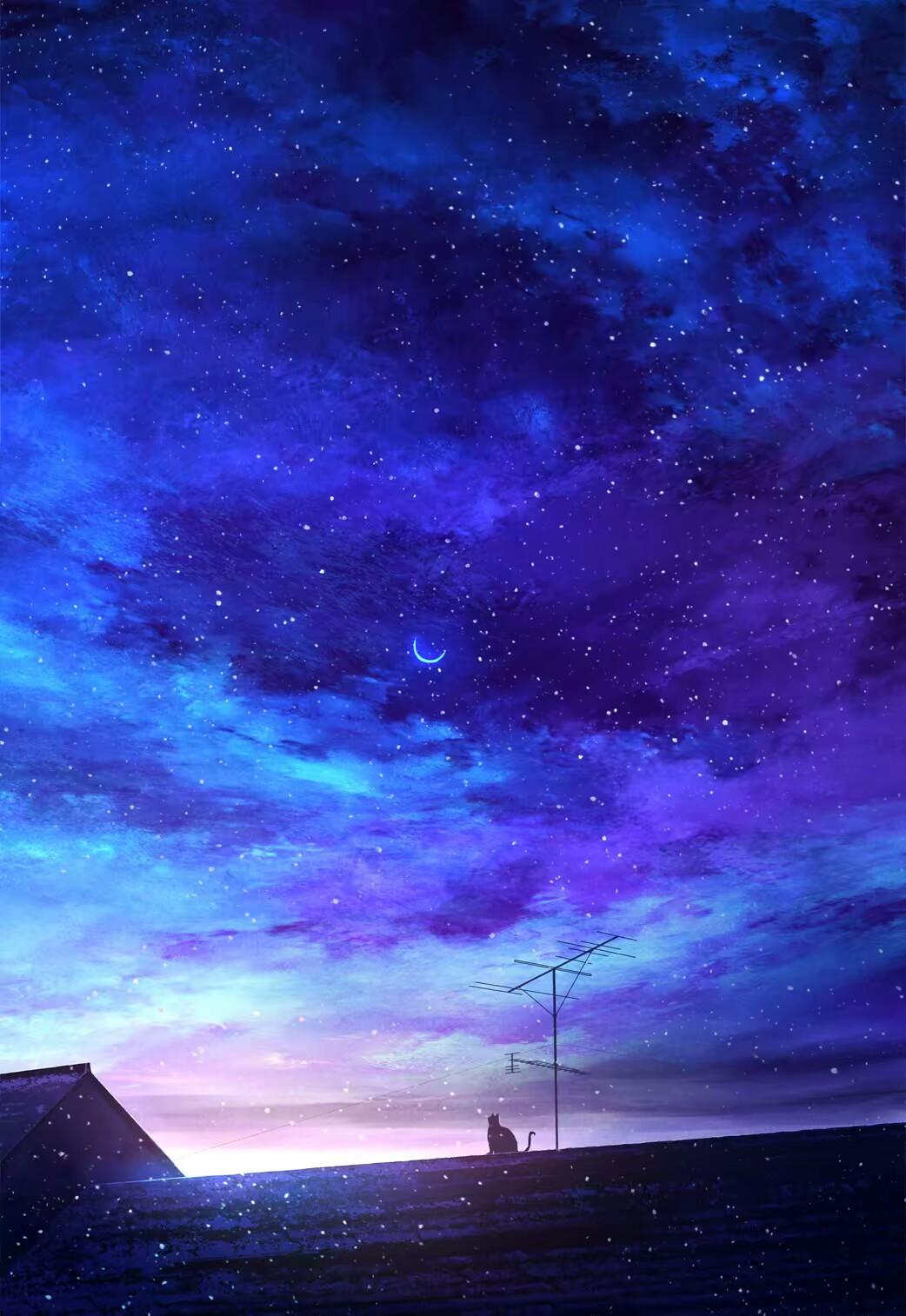车间墙角的铸铁扳手磨得发亮,木柄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。老周用粗糙的拇指摩挲着这些痕迹,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:“机器会生锈,但手里的活儿不能生。” 三十五年前那个雪夜,他在国营工厂的锻压车间第一次握紧铁锤,通红的钢坯在砧上发出滋滋的喘息,火星溅在蓝色工装裤上烫出星星点点的洞,像缀满了永不熄灭的星辰。
老周的工具箱里总躺着块帆布,褪色的蓝底上绣着 “精工” 两个黄字。这是母亲当年在灯下一针一线缝的,针脚里还藏着樟脑丸的气息。他记得刚当学徒时总把零件磨得歪歪扭扭,师傅不说重话,只是把自己的帆布罩在他的工具箱上:“等你能让游标卡尺认错,再换回来。” 后来他真的做到了,在全市技术比武里,他磨出的轴承公差比标准还小三个丝,评委用放大镜看了三遍才敢相信。
那些年的车间总飘着机油与铁锈混合的味道。凌晨三点换班时,锅炉的蒸汽会裹着月光漫进来,年轻的女工们趴在机床旁打盹,发梢沾着细碎的铁屑,像落了层银霜。老周见过最动人的景象,是老焊工老李戴着护目镜作业,弧光在他皱纹里流淌,焊花落在满地钢屑上,竟像在黑夜里种出了一片银河。那时的制造,是人与钢铁最亲密的对话,每道工序都浸着体温。
转折发生在新世纪初的某个清晨。当德国产的数控车床被叉车运进车间,老周听见齿轮转动的声音变了。不再有锻锤撞击的震颤,不再有砂轮打磨的锐鸣,取而代之的是伺服电机平稳的嗡鸣,像某种精密的呼吸。他试着按动操作面板,显示屏上跳动的数字让他想起刚上小学的孙子玩的电子游戏。那天中午,他把帆布罩收进了储物柜最深处,布角的线头勾住柜壁,扯出一根细长的纤维,在阳光下亮得像根银丝。
车间主任小陈总说老周是 “行走的工艺库”。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,电脑里存着三百多个加工方案,却总在遇到难题时往老周的操作台跑。有次进口设备卡了料,技术员捣鼓了半天没辙,老周摸了摸卡盘的温度,往齿轮箱里滴了三滴特制润滑油 —— 那是他用废机油混合蜂蜡熬的 “秘方”,机器果然重新转了起来。小陈拍着他的肩膀笑:“周师傅,您这手绝活,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” 老周却摇头,他看见小陈的电脑屏幕上,三维建模的零件正在虚拟空间里旋转,那些线条比他画在铁皮上的粉笔印要精确得多。
新招的 95 后技工小林,工位就在老周对面。这姑娘总戴着无线耳机,一边编程一边跟着节奏轻轻晃头,磨出来的刀具却比谁都锋利。有次老周见她对着屏幕叹气,凑过去才发现是个曲面加工参数总调不对。他没说话,拿起块废钢料在砂轮机上磨了个异形样板,小林眼睛一亮,照着样板修改了模型,问题迎刃而解。那天下午,小林给老周看她手机里的照片:她用 3D 打印机做的镂空书签,上面刻着 “匠心” 两个字,纹路细得能穿进绣花针。
去年冬天,车间接了批航天零件的订单。要求的精度达到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,老周和小林组了个临时搭档。老周负责手工研磨接触面,小林操控机床完成复杂切削。有天加班到深夜,小林忽然指着监控画面笑:“周师傅您看,咱们俩的动作重合率快百分之九十了。” 屏幕里,一老一少俯身工作的剪影渐渐重叠,老周粗糙的手掌与小林戴着超薄手套的手指,在零件上方划出近乎一致的弧线。窗外飘起那年的第一场雪,落在恒温车间的玻璃上,瞬间化成细小的水珠,像无数只眼睛在静静注视。
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上,老周第一次见到了协作机器人。银色的机械臂灵活地拧着螺栓,末端的力传感器能感知到纸片厚度的阻力。演示结束后,工程师邀请观众体验,老周犹豫着伸出手,当机械爪与他的手掌轻轻相触时,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握着他的力道。那一瞬间,钢铁的冰凉里似乎传来某种熟悉的脉动,像三十五年前那块被他焐热的钢坯。
现在的车间总飘着淡淡的松香水味。老周的储物柜里,帆布罩被小林绣上了新图案:传统的榫卯结构里,嵌着一行代码。他依然每天擦拭那把铸铁扳手,只是不再用它敲打钢坯,而是偶尔借给小林校准夹具。有次小林问他,会不会觉得现在的制造少了点什么。老周望向窗外,物流机器人正驮着物料在阳光下穿行,它们的履带在地面留下细密的纹路,像某种崭新的年轮。
暮色漫进车间时,老周习惯性地检查每个工位。在数控车床的废料盒里,他发现了块被切下来的钢屑,卷曲的形状像只正在振翅的蝴蝶。他小心地捡起来,放进那个装着帆布罩的储物柜。明天小林来上班时,或许会发现这个意外的礼物,或许会把它放进 3D 扫描设备,让这只钢铁蝴蝶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。而此刻,晚风穿过通风管道,带着远处锻造车间隐约的轰鸣,那声音里,有老周年轻时的心跳,也有属于未来的回响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