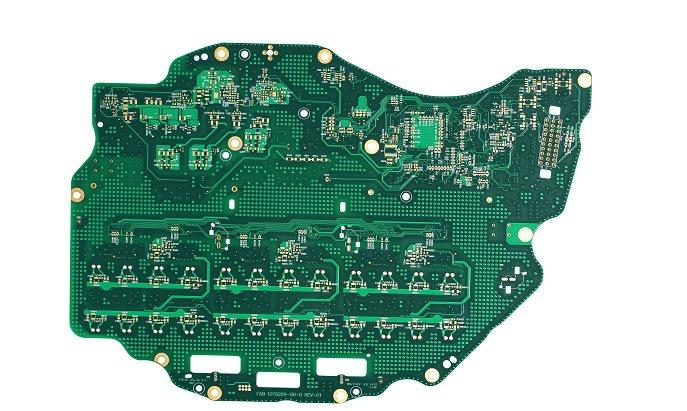老城区的青砖灰瓦间,陈阿婆的窗台总像被打翻的调色盘。早春有金边瑞香探出蜷曲的嫩芽,盛夏是茉莉把甜香浸进晚风,霜降过后,那盆蜡梅便攒着星星点点的金黄,等一场雪来就炸开满枝清冽。这些花草陪着她走过三十七个春秋,每片落叶都藏着光阴的褶皱。
1988 年的梅雨季节格外漫长,陈阿婆还在纺织厂当挡车工。某个中班结束的深夜,她在厂门口的垃圾堆里捡到株快蔫死的栀子。彼时丈夫刚去世半年,儿子在外地读大学,空荡荡的两居室里,只有挂钟的滴答声比雨声更寂寥。她把断了根须的栀子裹在湿毛巾里带回家,用搪瓷缸盛着清水养在窗台,竟在第七天瞧见新冒的白根。
那株栀子后来在陶盆里扎了根,第三年夏天开了四朵花。陈阿婆把最大的那朵别在儿子的衬衫口袋,送他去火车站。少年背着帆布包转身时,白花瓣蹭过肩头,留下淡淡的黄痕。“妈,明年我带女朋友回来瞧它开花。” 他挥着手钻进人群,陈阿婆望着那抹远去的背影,忽然发现栀子的香气里混着自己的眼泪,咸涩却温热。
纺织厂改制那年,陈阿婆提前退了休。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消失后,窗台的花草成了新的牵挂。她开始在清晨去城郊的花市,用攒下的退休金花五毛钱买一把康乃馨,或是用两个鸡蛋换邻居半袋营养土。有次暴雨冲垮了窗台上的木板,她踩着板凳伸手去捞那盆刚结花苞的米兰,后腰撞到窗框上,疼得直抽气,却死死把花盆抱在怀里。
儿子带未婚妻上门那天,陈阿婆特意剪了把粉色月季插在玻璃瓶里。女孩指着窗台那株爬满防盗网的三角梅惊叹:“阿婆,这花开得像瀑布!” 陈阿婆眯眼笑,说这是当年搬家时从老房子墙根挖来的根须,没想到能长得这么疯。吃饭时,女孩偷偷告诉陈阿婆,她妈妈也爱养花,就是总养不活。陈阿婆听了,第二天就把那盆最皮实的太阳花分了一半,用旧报纸包好让儿子带过去。
孙子出生后,窗台渐渐多了些耐阴的植物。陈阿婆怕那些带刺的玫瑰扎到孩子,移到了阳台外侧的花架上。小家伙刚会走路时,总踮着脚扒着窗台看那盆含羞草,手指一碰,叶片就唰地合拢,惹得他咯咯直笑。有次趁大人不注意,他揪下片茉莉花瓣塞进嘴里,被陈阿婆发现时,正皱着眉头吐舌头,说苦苦的。
去年冬天来得早,陈阿婆的关节炎犯了,没法再像从前那样每天搬着花盆晒太阳。儿子想请个钟点工帮忙,被她摆手拒绝了。“这些花认人呢,” 她摸着那盆养了十五年的栀子,树皮已经皲裂如老人的手,“它们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浇水,什么时候该松土。” 那天下午,阳光透过玻璃窗斜斜落在她和花盆上,影子在墙上依偎着,像幅安静的油画。
清明前,陈阿婆发现那株三角梅的枝条有些枯萎。她搬来梯子仔细查看,才发现根部被老鼠咬了个洞。看着那些曾经泼泼洒洒的花朵慢慢蔫下去,她没像往常那样掉眼泪,只是每天用棉签蘸着药水涂抹伤口。儿子来看她时,见她对着枯花发呆,劝她扔掉算了,再买新的。陈阿婆摇摇头:“它陪我走过最难的日子,我得等它自己做决定。”
谷雨过后的某个清晨,陈阿婆推开窗,忽然发现三角梅枯黑的枝条顶端,冒出个米粒大的绿芽。她愣了半晌,摸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,声音里带着哭腔,却笑得像个孩子。挂了电话,她转身去厨房找剪刀,想把旁边的绿萝挪开些,好让这株劫后余生的花多晒点太阳。
窗台上的风信子正在开花,淡紫色的花穗沉甸甸地低着头。陈阿婆修剪枝叶的手微微颤抖,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泛起一层柔和的银光。楼下传来卖花人的吆喝声,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,她忽然想起刚搬来这里的那年,也是这样的时节,空气里飘着花草的清香,日子像刚浇过水的泥土,松软而充满希望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