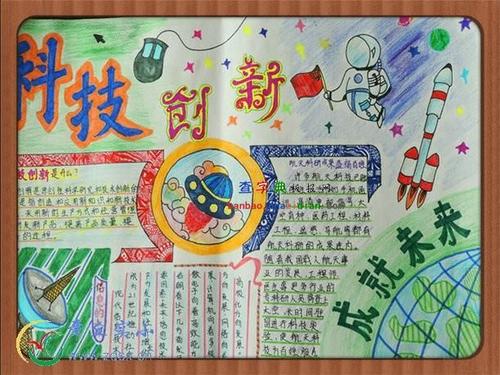阿古拉家的蒙古包外总是拴着两匹老马,枣红色的那匹叫 “风影”,鬃毛里还缠着去年深秋的草籽。清晨的露水打湿马镫时,七十岁的阿古拉会牵着它们走向围栏,木栅栏上的裂纹里嵌着三十年前的羊粪,经岁月打磨成了深褐色的琥珀。
牧场的晨雾里藏着太多故事。阿古拉的祖父那顺是在马背上讨生活的人,民国二十六年的那场雪灾过后,他用三件羊皮袄换回了第一群羊。那些羊的蹄子上都带着伤,在结了冰的河面上留下点点血痕,却把根扎在了这片叫 “呼和塔拉” 的草原上。那顺总说羊是通灵性的,有年春天狼群来袭,头羊竟带着羊群钻进了牧民废弃的窑洞,等他带着猎枪赶到时,窑洞门口堆着二十多只小羊羔,全是母羊用身体护住的。
阿古拉的父亲巴图赶上了集体牧场的年代。那时的呼和塔拉竖起了铁丝围栏,拖拉机的轰鸣声第一次盖过了马头琴。巴图成了牧场的放牧组长,胸前别着亮闪闪的搪瓷徽章,上面印着 “劳动模范” 四个金字。他发明了用芨芨草捆扎饲料的方法,能让羊群在冬春之交多撑半个月。有年夏天暴雨冲垮了草料库,巴图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抢救麦秸,等他爬上岸时,怀里还紧紧搂着一袋刚出生的羔羊奶粉。
阿古拉十岁那年第一次独自放牧。父亲给他的牧羊犬叫 “黑炭”,是条半大的狼狗,却总被羊群里的头羊欺负。那天他追着跑散的山羊闯进了陌生的山谷,直到月亮升起来才发现找不到回家的路。黑炭突然对着一处崖壁狂吠,他走过去才看见,母羊正用前蹄刨着岩石缝,里面藏着三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羊羔。后来他才知道,那是前几天被狼群惊吓跑丢的羊群,母羊竟带着孩子在崖壁下守了三天。
八十年代末的草场开始显露出疲惫。阿古拉跟着父亲去旗里开会,第一次见到了 “草原沙化” 这个词。回来的路上,他们看见原本水草丰美的西坡露出了成片的黄土,像老人脸上脱落的皮肤。巴图蹲在地上抓起一把土,指缝间漏下的沙粒簌簌作响,他说这是羊太多了,把草连根都啃没了。那年冬天,阿古拉家主动削减了一半的羊群,母亲心疼得直抹眼泪,那些要被送走的羊里,有只母羊刚生下双胞胎。
新世纪的风带着新变化吹进草原。阿古拉的儿子乌日根从兽医学校毕业,背着药箱回到牧场时,还带回了一台笔记本电脑。他给羊群建立了档案,每只羊的耳朵上都戴着写着编号的耳标,电脑里存着它们的出生日期、健康状况,甚至还有繁殖记录。阿古拉起初不理解,觉得羊就是羊,记那么多东西有啥用。直到有年春天爆发口蹄疫,乌日根靠着档案迅速隔离了病羊,家里的羊群才躲过一劫。
乌日根在牧场里搞起了生态养殖。他拆除了部分围栏,让羊群在划定的区域里轮牧,还种上了沙打旺和紫花苜蓿。这些外来的草种起初被老牧民嘲笑,说它们开的花再好看也填不饱羊肚子。可到了秋天,种着苜蓿的地块比别处高出半尺,枯黄的草叶下藏着密密麻麻的新芽。阿古拉牵着风影走过那里时,发现有只瘸腿的母羊正领着小羊啃食苜蓿的根,那是去年冬天被狼咬伤的羊,竟在这片草地上养好了伤。
去年夏天,旗里来人考察,说要在呼和塔拉建生态旅游区。乌日根召集牧民开会,提出搞 “牧家乐”,让游客体验放牧生活。阿古拉坐在最前排,听着儿子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计划,突然觉得他说的那些 “可持续发展”“生态经济”,其实和祖父那顺说的 “羊要吃草,草要扎根” 是一个道理。会后他走到草场边缘,那里新栽的沙棘苗已经长到齐腰高,叶片上还挂着晨露,远处的羊群像流动的白云,缓缓漫过青翠的山坡。
傍晚的牧场总带着淡淡的奶香。阿古拉看着乌日根给刚出生的牛犊喂奶,塑料奶瓶里装着温热的代乳粉,小家伙却挣扎着要去舔母牛的乳头。风影在一旁甩着尾巴,它的鬃毛里又沾了新的草籽,是今年雨水好,草长得格外旺盛。远处的蒙古包里升起炊烟,母亲正用传统的方法熬制奶豆腐,酸香的气味随着风飘过来,和草原上的青草香混在一起。
羊群归栏时发生了件趣事。有只刚学会走路的小羊羔,非要跟着风影走,无论母羊怎么叫都不回头。阿古拉笑着解开马缰绳,风影会意地迈开步子,小羊羔果然颠颠地跟在后面,母羊无奈地摇摇头,只好跟在它们身后。夕阳把它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马的影子,羊的影子,还有站在围栏边的人的影子,都融在渐渐暗下来的草原里。
夜色像巨大的毯子盖下来时,蒙古包里亮起了灯。乌日根在电脑前整理明天的放牧计划,屏幕上跳动着的数据映在他年轻的脸上。阿古拉坐在旁边擦拭着祖传的套马杆,杆头的铜箍被磨得锃亮,上面刻着的花纹已经模糊,却还能看出是三匹奔跑的马。外面传来黑炭的低吠,大概是晚归的羊群惊扰了它的美梦,紧接着又响起母羊温柔的呼唤,像在哄着不听话的孩子。
草场上的风还在吹,带着千年不变的节奏。阿古拉想起祖父说过,草原就像有生命的东西,你对它好,它就给你回报。他不知道乌日根规划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,但他看见月光下的草叶上,正凝结着新的露水,而那些埋在土里的草籽,已经在等待明年春天的召唤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