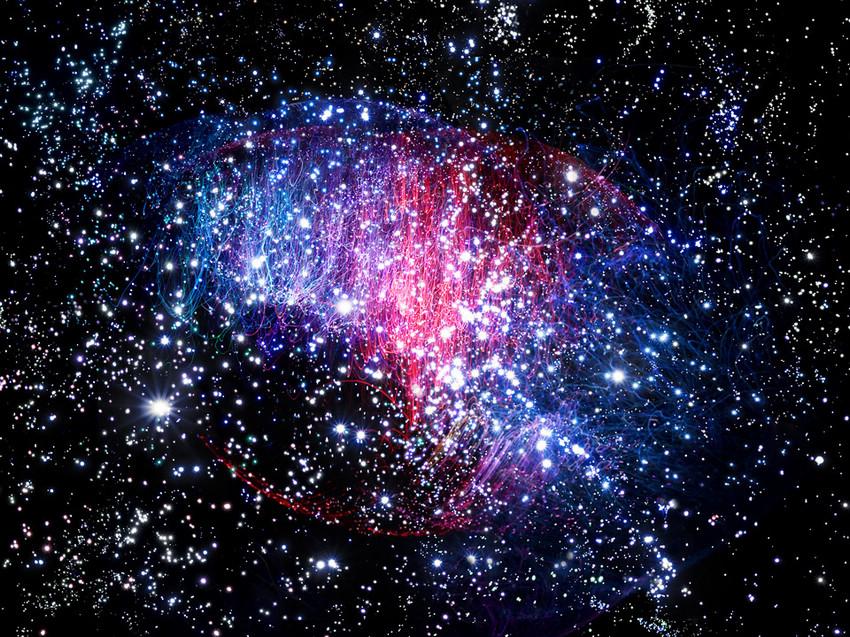晨露坠在稻叶尖端时,整个村庄还浸在蓝灰色的梦里。竹篱笆上的牵牛花蜷着浅紫的瓣,像未拆的信笺,要等第一缕阳光吻过黛瓦,才肯舒展藏了整夜的私语。老井轱辘上的麻绳结着经年的包浆,井台青石板的凹痕里,盛着昨夜星子遗落的碎银。
村口的老槐树总比别处醒得早。虬曲的枝桠托着半透明的雾,叶隙漏下的光在泥地上洇出细碎的金斑,像谁撒了把碾碎的朝阳。穿蓝布衫的阿婆提着竹篮走过,布鞋踩过带露的草,惊起几只蚂蚱,蹦跳着躲进田埂边的野菊丛。竹篮里的新摘豆角还沾着湿土,紫莹莹的茄果泛着瓷光,都是从屋后菜园刚掐下的鲜活。
春深时,油菜花海把天地染成琥珀色。风过时,花浪推着香气漫过石桥,漫过晒谷场,漫过青砖墙上斑驳的标语。戴草帽的农人弯腰插秧,泥水裹着裤脚,倒影在水田里轻轻摇晃,与掠过的白鹭共成一幅流动的画。田埂上的蒲公英举着白绒球,被孩童的笑声惊得散作星雨,落在姑娘们编着麻花辫的发间。
溪涧是村庄的血脉。青石板铺就的溪埠头,木槌捶打衣裳的声响惊起石缝里的小鱼,尾鳍一摆便没入碧色深处。浣衣的妇人挽着袖口,手臂上沾着皂角的白沫,家常话随着溪水潺潺流淌,绕过石拱桥的拱券,又从下游的芦苇荡里荡回来。蜻蜓停在她们红蓝相间的晾衣绳上,翅膀透明得能看见阳光的纹路。
炊烟是村庄最柔软的轮廓。黄昏漫过晒谷场的谷堆时,各家屋顶升起的烟在暮色里轻轻缠绕,像谁用毛笔蘸了淡墨,在青灰色天幕上晕染开的笔触。灶间飘出柴火的气息,混着新蒸的米香与腌菜的微酸,勾得放学的孩童加快脚步,书包带子在身后颠出欢快的节奏。竹椅在晒场上排成蜿蜒的长龙,老人摇着蒲扇讲古,故事里的狐狸总爱在月光下偷喝农家酿的米酒。
夏夜里的星空低得仿佛伸手能摘。晒谷场的竹席上,孩子们数着流星划过银河的轨迹,萤火虫提着灯笼从玉米地飞来,与天上的星子分不清彼此。蛙鸣在稻田里涨成潮汐,蝉声藏在柳荫里织成网,偶尔有晚归的牛铃从巷口传来,叮当声漫过熟睡的菜园,惊起竹篱笆上的纺织娘,续上被打断的夜曲。
秋收的日子,田垄铺着金色的绸缎。脱粒机的轰鸣里,谷粒跳跃着坠进麻袋,扬起的谷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木耙在晒谷场画出规整的纹路,像大地晾晒的琴谱,风走过时便弹出沙沙的乐章。屋檐下挂满金黄的玉米与火红的辣椒,像谁把整个秋天的色彩都串起来,晾晒在时光的绳上。
老祠堂的天井里,青苔爬满石雕的柱础。雕花窗棂漏下的光,在青砖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,与香案上摇曳的烛火缠绵。供桌上的青花瓷瓶插着时令的野花,清明是杜鹃,端午是艾草,重阳是野菊,岁岁年年,把四季的芬芳敬给沉默的祖宗牌位。梁上的燕子窝换了几代主人,呢喃声里藏着村庄最悠长的记忆。
冬雪落时,村庄便成了水墨画。黛瓦上的雪被风梳得整整齐齐,像谁铺了层绵密的白糖,檐角垂下的冰棱是透明的玉簪,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虹。篱笆上的枯藤挂着冰晶,偶尔有麻雀落在上面啄食,抖落的雪沫簌簌掉进炭火盆里,化成一缕轻烟。火塘边的陶罐咕嘟作响,新酿的米酒在陶瓮里沉睡着,等待开春时与桃花共醉。
巷弄是村庄的掌纹。青石板路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发亮,凹处积着雨水,倒映着飞翘的屋檐与流动的云。斑驳的木门上,春联的红褪成温柔的粉,门神的眉眼在风雨里渐渐模糊,却依然守着门内的晨昏。猫蜷缩在门槛上打盹,尾巴圈住整个冬天的暖阳,偶尔睁眼看看路过的黄狗,又懒懒地闭上,把时光也眯成了一条缝。
春日的雨总带着草木的清香。油纸伞在巷子里开出五颜六色的花,鞋跟敲在青石板上,溅起的水花沾湿裤脚,带着微凉的诗意。桃花瓣被雨打落,飘在积水里打着旋儿,与屋檐滴下的水珠共舞。卖花的阿婆披着蓑衣,竹篮里的茶花沾着雨珠,花瓣肥厚得能挤出春天的汁液,递过来时,带着满手潮湿的芬芳。
暮色漫过石桥时,洗衣妇的木槌声渐渐稀疏。溪水带着最后一缕天光流向远方,芦苇荡里的野鸭把头埋进翅膀,准备在星光下安歇。谁家的窗棂透出昏黄的灯光,像大地睁开的惺忪睡眼,在无边的夜色里,守着一个又一个温柔的黎明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